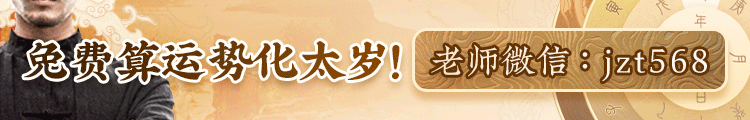鼎盛千秋铜摆件(鼎盛千秋铜摆件值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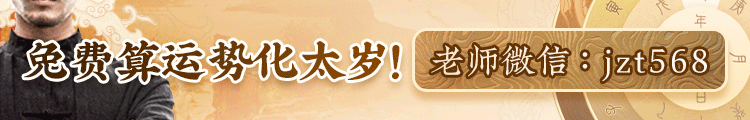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来介绍鼎盛千秋铜摆件(鼎盛千秋铜摆件值钱吗)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来看看吧。
文章目录列表:
- 1、70年看上博①|“鼎盛千秋”背后的青铜文物修复技艺与传承
- 2、被誉为“国之重器”,商周青铜器凭借的不仅仅是重量
- 3、被誉为“国之重器”商周青铜器凭借的不仅仅是重量
- 4、青史斑斑|鼎盛千秋:西周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
- 5、国之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重聚,上博将展出21件有铭青铜鼎
70年看上博①|“鼎盛千秋”背后的青铜文物修复技艺与传承
澎湃新闻记者 陈若茜 陆林汉 实习生 刘畅
视频加载中...
作为一家海内外驰名的大型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自1952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以收藏、保护、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为己任,且尤重文物研究与保护的传承,七十年传承,文脉在兹。以文物修复而言,之所以代代相传,即得益于一直以来的师徒传承,而且有传承,也有创新。
澎湃新闻从今天起,陆续刊出系列报道“70年看上博”。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走过近七十年的历程,上海博物馆以追求卓越、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姿态,赢得了全球美誉。审视当下,她更加彰显人民的立场、世界的眼光,正构建“一体两馆多点”新格局,攀登新高峰。展望未来,她将是顶级的艺术殿堂,同时还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学习知识的课堂、交流思想的会堂、休闲娱乐的厅堂。她是人类灿烂文明的守护人,也是参与创造新时代、新文化、新生活的建设者。”
02:41
视频加载中...
上海博物馆第二代青铜修复师黄仁生谈复制大克鼎往事。 编辑 陆林汉(02:41)
7月25日,送走展厅内最后一批观众,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也将暂别上海,随大盂鼎一起移师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展”是上博今夏推出的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短短一个半月展期,吸引了数十万名观众前来参观。
在展览闭幕前夕,88岁高龄的上海博物馆第二代青铜修复师黄仁生在两位弟子的陪同下来到展厅,师徒三人绕着两方大鼎转了好几圈,除了偶尔交谈,更多的时候只是静静凝望。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展”展览现场,大克鼎与大盂鼎
黄仁生(中)与学生张珮琛(右)、陆耀辉(左)在展厅内的合影
对于大半辈子都在跟青铜器打交道的黄仁生而言,大盂鼎和大克鼎在其心中的分量不可估量。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大盂鼎和大克鼎入藏上博之后,黄仁生就曾亲手对大盂鼎做过清洗,而原大的大克鼎第一件复制品也出自黄仁生之手,对于一位文物修复师而言,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上博修文物40余年,黄仁生经手、修复过的青铜器不计其数,也不遗余力地为上博培养了第三、第四代修复师。如今他的好手艺在弟子身上得到传承,他们接过师父手中的接力棒,为这项古老技艺注入新的活力。
一
米寿之年的黄仁生精神矍铄,一口夹杂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与身旁张珮琛、陆耀辉两位弟子言笑晏晏。三人戏言,在上博从事青铜器修复的老先生们总是特别高寿,因为他们一直在做给文物“续命”的善行。这当然只是谈笑。
谈及时隔多年,在展厅内看到双鼎合璧展出,心里作何感受?黄仁生说,“作为文物工作者,能够清理好这两件大鼎,还能有这么多观众来参观,内心是很激动的。”
走出展厅,黄仁生经过展厅入口处的海报,眼尖的他一眼就看到海报上大克鼎纹饰的线图,说:“要画准确青铜器的纹饰最不易。一般人看这线图可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我们搞青铜器修复的人看来还是外行画,太生硬。”一旁的张珮琛、陆耀辉也是心领神会。
“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首先要过的就是纹饰这一关。”黄仁生说,当年他跟随师傅王荣达学艺,就是从学画青铜器纹饰开始。白天在馆里上班,业余还要对着厚厚的青铜器图录画纹饰。“画纹饰的目的是为了熟识不同时代的纹饰风格。纹饰画得不对,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对路。”
黄仁生出生于1933年,进上海博物馆之前他已经是上海标本模型厂比较资深的技师,专门从事人体医药卫生模型的制作,待遇很不错,拿的是八级工人的工资。
1958年,上海博物馆设立文物修复工场,组建了书画装裱、平面修复、青铜陶瓷修复三个小组,于是将社会上一批功力深厚、技艺高超的手艺人汇集到博物馆,黄仁生就是在那时候被招进上海博物馆,进馆时刚刚25岁。因为懂雕刻,懂磨具翻印,所以被分配到青铜陶瓷修复组,师从馆内老先生王荣达。
黄仁生
黄仁生在复制青铜器
进馆后不久,由于要对大盂鼎做清洗工作,黄仁生初次见到了历经跌宕起伏的盂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均为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清朝时期从陕西出土,后为苏州潘氏家族收藏。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代表家族将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黄仁生说,“大盂鼎多年来一直在潘家保存,保存状况很好。当年潘家为了躲避日本人搜查,一度将其入土埋藏,所以鼎的表面附着了一些泥土,我们只是把泥石简单清理了下,看上去就蛮好了。”
潘达于和大盂鼎、大克鼎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
黄仁生复制大克鼎的时间则要更晚些。为什么要复制大克鼎呢?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基本国策。为了“备战”,防止文物遭到战争破坏,上海博物馆要另外造一处保密库房,凡是等级比较高的文物统统放到保密仓库里保管。为了不影响展览,上海博物馆复制了好多件文物,复制大克鼎的重任就落在黄仁生身上。
由于受当时经济等条件的限制,用青铜来复制青铜鼎是不可能的,所以黄师傅是用石膏复制。石膏模型出来后又经过上色、做旧、上锈等多道工序,整个过程耗费了四五个月,出来的效果几乎可以“乱真”。
“应该说,复制好之后,包括专家在内,大家对大克鼎复制品的评价都很高,都说大克鼎复制得好。”谈及此,仍能感受到黄仁生内心的骄傲之情。
不过“文革”期间,黄仁生却因此没少挨过批判。“他们批判我的重点全在大克鼎上,说我只重视业务不重视政治,所以才把大克鼎复制得这么好。而且还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大克鼎党员’。”时过境迁,黄仁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趣闻来谈,但也足见老先生的手上功夫不一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时代发展,复制件已经渐渐退出文博机构的展陈,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克鼎复制品也早已完成使命,撤出展厅。
上海博物馆第二代青铜修复师黄仁生在大克鼎前
二
在进馆之前,黄仁生是在模型厂做医药模型的,并没有接触过文物和文物修复,师父王荣达是他在文物修复领域的领路人。“我的师傅跟我是同一年进馆,但他比我大一轮,也属鸡。”黄仁生说。
王荣达在进上海博物馆前,就已经是上海滩古董行修复青铜器的业内高手了。他的修复技艺可溯源至清宫修复师“古铜张”一脉。
据张珮琛介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地区的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水准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其历史可追溯到清末内务府造办处设立的古铜局,其中有一位名为“歪嘴于”的巧匠为宫中修复和仿制了许多古铜器。其弟子张泰恩继承衣钵,被世人称作“古铜张”。王荣达是“古铜张”的再传弟子,他出师后,来到上海为古董行修复青铜器。1958年,因上海博物馆设立文物修复工场的契机,王荣达作为业内高手之一被聘入上海博物馆。
“师父是我的领路人。”黄仁生说,“他是做文物修复的行家,他干活的时候我们就在一旁观察,他讲这个底子应该怎么做,我们就照做。只要是不知道的、不懂的都去学。”
得益于原来在标本模型厂的工作经历,黄仁生将师父教授的文物修复技艺与原本在标本模型厂中掌握的模具与精密铸造技艺进行融合、创新,使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艺在工艺水平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上博独树一帜的技艺特点。
黄仁生(右)与马承源(左)
黄仁生与“九龙宝鼎”
黄仁生提到,要想胜任青铜器的修复与复制工作,非常不容易。尤其要达到专家一级的水准,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还要肯钻研。
“青铜器的修复,最难的是要做到和原件一致,这就要求我们首先纹饰要画准确,符合年代风格,许多错误的修复案例,就是没有研究不同时代的纹饰风格;其次要会雕刻,手工雕刻出的纹饰要和原件一致;第三要懂色彩,比如复制大克鼎要给它上色,如果不懂色彩搭配就做不到外观上的相像;第四,要懂模具和铸造,会根据不同的青铜器选择不同的铸造方法。最后还要懂化学,要给青铜器除锈、做锈,如果不懂化学知识,锈没去好,还可能损坏文物的皮壳……。”
黄仁生(左2)在复制青铜器
黄仁生的手艺不仅得到师父的认可,也获得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青铜器专家马承源的赏识。他们曾在马承源先生的指导下,成功为广州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复制铸造大克鼎等比放大7倍的“九龙宝鼎”。
龙流盉,上海博物馆藏
此外,黄仁生修复过上博馆藏的春秋中期兽面纹龙流盉,成功复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名品厚趠方鼎等。
兽面纹龙流盉是一件春秋中期南方越族人模仿西周盉并加以创造的杰作,从前这件器物被看成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随着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件器物所具有的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特点被不断认识。“从纹饰而言,这件器物上的兽面纹与中原商朝和西周时期的兽面纹大相径庭,是一种南方特色的装饰。”
龙流盉,上海博物馆藏
“这件器物修复前缺损比较严重,修复难度极大,花了两年时间。器物的修复过程几乎涉及修复技艺的所有工序,是综合体现青铜器修复技艺的代表性案例。”黄仁生说。
厚趠方鼎在宋代即已著录,流传保存至今近千年,极为罕见。此次“鼎盛千秋”特展上其与大盂鼎、大克鼎共同展出。黄仁生用传统工艺复制的厚趠方鼎也可谓形神兼备。
“我们搞(青铜)修复的人,想做得完美高级,是不简单的。只有沉下心,钻进去看,才会发现这些文物是非常好、非常妙的。”黄仁生用简单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几十年实践的真谛。
三
上博的文物修复何以代代相传,技艺不灭?这得益于文物修复团队从建立之初就确立的师徒传承的方式。不过与很多“固守成规”的文物修复流派不同,上博的文物修复技艺既有传承,也有创新。
黄仁生不遗余力得为上博培养第三、第四代修复师,带过的徒弟不下十几人,许多已成为国内外文博机构的业务骨干。其中,张珮琛现为上博青铜器修复的第三代传承人,自1993年进入上博工作至今,已经从事了28年的青铜器修复工作,多次参与国家重大考古项目,经手的文物有上千件,修复了战国时期的兵器商鞅铍、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青铜龙纹禁等。
陆耀辉1996年进入上海博物馆艺术品公司,师从黄仁生学习青铜器复制技艺。从业至今25年,他独立完成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邵钟、冒鼎、垣上官鼎、陈纯釜、镶嵌棘刺纹尊等重要青铜器的仿制工作,也曾帮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山西青铜博物馆等仿制青铜文物。
黄仁生(左)与学生张珮琛(右)
黄仁生与学生在上博展厅内交流
当年作为业内高手进入上博的王荣达修复造诣极高,尤其对青铜器纹饰和形制研究至深;黄仁生进馆后,也是从研究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起步,一步步走上文物修复的道路;等到黄仁生带徒弟时,也非常强调对青铜器纹饰的研习。
张珮琛和陆耀辉谈到,他们第一天见师父,师父就拿了两本书:《上海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和《中国青铜器纹饰》。师父说,你们既然要做这项工作,先把那两本书拿过去学习一下。几天之后,师父又让每人去复印十组图案再临摹一遍。
“开始拿到图案,我们觉得学了多少年的美术,没有什么难度。但当你画的时候,你就知道青铜器图案的难度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陆耀辉说,“虽然图案已经从立体翻到平面,三维变成二维,应该简单了好多了,但当你画的时候,你就发现没那么简单,得反复练习加思考。”
“师父这样的老一辈手艺人,他说的能力并没那么强,但是做的能力很强。他做的手艺在内行和外行看来都是很精彩的,所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师父的手上功夫,经常是他做的时候我们在一旁观摩,从他做的过程中来思考自己的不足。他这种身体力行的授业方式也体现了老一辈的匠人本色。”张珮琛说。
在技艺上,他们继承了师父的衣钵,但在行事风格上,他们跟师父等老一辈手艺人相比存在很大区别:“师父对于工作循规蹈矩,他的工作台每天都清理得干净整洁,工具也摆放得井井有条;师父做得多说得少,很少蹦什么金句格言,通过身体力行,润物无声地将文物修复理念传授给后辈了。”
而像张珮琛这一代的文物修复师,很多都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审美和态度,拥抱新科技。他们也愿意在公共平台去发声,宣传自己的文保理念。比如张珮琛其实就是一直活跃在微博上的大V“文物医院”,不少文博从业者和爱好者都会关注他的动态,看他就一些文物事件分享自己的观点。而之所以取名“文物医院”,是因为他觉得文物修复师最好的比喻就是“文物医生”,尽量利用一些现在的技术或者方法,消除或是延缓文物的一些病害,保存文物的价值。
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龙纹禁组里户方彝(修复前)
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龙纹禁组里户方彝(修复后)
师父年近九旬还在计划制作新的器物,陆耀辉说,老手艺人这种艺无止境的精神令他这个晚辈动容。反观自身,他对青铜器复制技艺的求索,也早已超越当年为艺术品公司生产售卖复刻品的最初目的,他希望对青铜器文物的仿制能尽可能回到时代语境,用相近的工艺,模仿历经几千年的斑驳锈色,只要能够跟原物更接近,或者给人带来更多美的享受,就是他从艺多年后仍不断追求精益求精的目标所在。
如今,上海博物馆的青铜修复和复制技艺已经传承到第四代,每一代修复师的传承如同不断补充的新鲜血液,从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创新的翻模工艺,到第三代修复师们擅长的美术技法,再到下一代的现代文保科技等,使得这项传统技艺不断得吐故纳新,成为一项既传统又科学的技艺。
大克鼎三份之一大复制件
冒鼎(复制件)
亡智鼎(复制件)
将近一个甲子的时光,从黄仁生复制第一件原大大克鼎,到如今师徒仨在展厅见证盂克双鼎的重逢,宛若一个小小的轮回。时光不曾为谁停留,但展厅内的盂克双鼎,在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悉心呵护下,风采却是丝毫不减当年。
对话|青铜器文物“厚趠方鼎”的复制和新技术在传统技艺中的运用
澎湃新闻:青铜器复制具体包含哪些步骤?
黄仁生:传统青铜器复制工艺流程可分为模范(造型雕塑,纹饰雕刻,石膏模翻制,石膏模精修加固)、失蜡铸造、(蜡模压铸,浇冒系统设计,涂料涂挂,脱蜡焙烧,铜液浇铸,浇冒口切割)仿古做旧(整形打磨,底色制作,手工堆锈,整体调整)。
澎湃新闻:您当年是如何复制厚趠方鼎的?
黄仁生:我们复制厚趠方鼎的时候,需要先把真品的样子大概取模翻制下来,再做成石膏,然后在石膏上进行修整。因为在原件上直接翻制下来会有很多缺点,翻出来的模具也有很多问题,所以要修整。修整的时候,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来修整,而要根据原件上面的纹饰,来看哪里有缺损、有不足,修整好之后就能使得最后的铸件成为一件比较好的复制品。像我们做复制品和普通文物商店的卖品是不一样的,原件上的锈是什么样的,复制品上我们就一定要做成什么样。
厚趠方鼎,上海博物馆藏
澎湃新闻:那你们是怎么做锈的?
黄仁生:青铜器上的锈总共有六七类,比如红锈、绿锈、石灰质锈。青铜器上的锈,最宝贵的是蓝锈,但是漂亮的蓝锈是很少见的,包括大盂鼎和大克鼎也很少看到漂亮的蓝锈。所以我们修复去锈的时候,看到蓝锈,都是要保护而不进行去锈。其次是绿锈,但是绿锈的保留需要考虑美观、对称和均衡。如果青铜器上的是大片的绿锈,就要去掉一部分,所以去绿锈的时候,要提前想好哪个地方要保留。
澎湃新闻:您在复制带铭文的青铜器时是怎么处理铭文的?是通过手工雕刻吗?
黄仁生:如果可以在文物上进行操作的话,我们就用一种医用打样膏加热回软后按上去,冷却之后取下来,但也像石膏翻模的青铜器一样需要观察其是否有缺点和不足,并对其进行修整。
澎湃新闻:像3d打印这类技术在青铜器复制中有没有应用?
陆耀辉:3d打印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但是要说复印性的话,还是像师傅这样传统的办法比较好,复印性是最好的,因为是直接在原样上取样和刻划,损失的细节是最少的。但是现在的文物复制必须要求对文物原件是非触摸式,所以我们这一代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与3D等技术更好的融合。
黄仁生:是的,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用好这些现代化的技术。不过这些现代化的技术在我们的复制工作中也有缺点。因为我们尝试过用3d打印复制陶器,陶器复制出来的纹饰和原来的有不同,样子也很生硬。所以3d打印一类的新技术很好,我们应该好好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技术,但是传统技术不能丢,3d打印出来之后还是要根据传统方法做成石膏,重新对照原件进行雕刻修整,而且要反复修整,直到和原件完全一致的地步,才算完成了复制。我们对纹饰复制的要求是极度准确的,但现在的3d打印还到不了完全准确的地步。
陆耀辉:3d打印的细节不足,原因就像早期数码相机一样,比如在青铜器的纹饰上,就到不了我们要求的那个精度。所以现在还是用师傅传下来的技术,通过手工雕刻来解决。
利用3D打印进行蜡模输出
澎湃新闻:明年(2022年)上海博物馆将迎来建馆70周年,据悉,上博正在筹备70件文物看上博的相关展览,从您的经历和研究出发,希望看到哪件馆藏文物亮相?
黄仁生:我比较推荐龙耳尊,春秋早期时期吴越青铜器,上博收藏有器型和纹饰相同的两件,是50年代老一辈专家从金属冶炼厂的废旧铜料中抢救回来进行了修复,我建议成对展出。
陆耀辉:我推荐良渚文化青浦福泉山吴家场墓地m207出土的象牙权杖。良渚博物院,上历博,青浦博物馆,福泉山遗址博物馆都陈列有它的复制品。目前象牙材质的权杖这是国内保存下来唯一的一根。
张珮琛:我推荐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隆平寺地宫出土的北宋铅贴金阿育王塔。隆平寺塔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塔的体量超过目前上海所存的13座古塔,这也是上海第一次经考古发掘确认的古塔遗址。塔基地宫出土的阿育王塔,通高25 厘米,底座长9.5 厘米。塔的材质含铅量超过90%,分片铸造,焊接成形后再通体贴金,这一制作方法在考古发现中罕见。
责任编辑:顾维华
被誉为“国之重器”,商周青铜器凭借的不仅仅是重量
中国国家博物馆“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让国博所藏大盂鼎与来自上博的大克鼎联袂亮相,图为展览海报
最近半年以来,商周青铜器备受关注。继上海博物馆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让国博所藏大盂鼎与上博所藏大克鼎联袂亮相,引发广泛关注后,眼下,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这几个大展不约而同聚焦商周时期最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风貌。
商周青铜器素有“国之重器”之称。它们中的不少的确有着惊人的体量,例如子龙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和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重201.5公斤)三鼎,但这毕竟浮于表面。商周青铜器之“重”,更在于极为丰富而厚重的历史积淀,有着从本质上体现其作为国之瑰宝的重要特征。
最能体现商周青铜器内在价值的,当属其中丰富铭文包含的文献信息
其实,单凭一尊毛公鼎就足以破除有关重器之“重”的迷思。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它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为“海内三宝”,但与盂、克二鼎相比,毛公鼎“仅”重34.7公斤,高53.8厘米,口径47厘米,在重量方面就比前两者足足少了一位数字。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毛公鼎却占有一项三鼎之最,那就是字数。据统计,三鼎内壁所刻铭文分别是497(毛公鼎)、291(大盂鼎)和290(大克鼎)字(引自杜迺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毛公鼎铭文字数不但冠绝所有商周青铜鼎,而且也是中国所有已知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按照杜迺松的说法,毛公鼎铭文数量“实可相当《尚书》一篇”。而盂、克二鼎虽不能在青铜器中占据次席(现存字数第二多的,是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散氏盘),但在现存铜鼎中却能紧随毛公鼎之后,分列二三(因为铭刻四百余字的周康王时器小盂鼎,四百十字的周共王时器曶鼎,都已于清末亡佚,仅铭文拓片存世)。
商周青铜器内壁往往刻有铭文,包含着丰富的文献信息(摄影:陈拓)
除了铭文字数之外,这些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同样体现了它们不凡的分量。按照原器所铸时间来看,大盂鼎最早,为周康王时器。记载了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康王先是赞美文、武先王,然后总结了商代覆亡的经验教训,告诫盂要引以为鉴,不能沉湎于饮酒取乐。这部分铭文内容恰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吻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次,又授予盂掌管兵戎、民事的权力,辅佐周王管理天下。最后还赐予了他代表权威的鬯酒、命服、车马等等,以及各类奴隶1726人,其中既有夷人的头领十三,也有夷众上千。
而大克鼎年代次之,为周孝王时器。讲述了贵族克继承先祖师华夫的官职,并被周王授予“膳夫”之职,获得诸多田地人口的事情。孝王首先赞扬克的祖先侍奉恭王,因而提拔克为王臣,负责传达王命的要职。接着重申了对膳夫克的任命,详细记录了对他的赏赐,包括礼服、土地和奴隶等等。最后是克叩跪感谢,铸鼎以纪念其先祖师华夫。
三鼎中的毛公鼎相对最晚,为周宣王时器。它记录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改变西周后期的种种弊政和不利局面,策命重臣毛公,监督各种政令的发布和实施。希望在毛公的忠心辅佐下,使国家免于衰颓的境地。最后为了体现对毛公的尊重,宣王还赐给他极为丰厚的赏赐,包括各种宝物和贵重的车马器。而毛公为了回谢周王,特意铸鼎记录此事。
三鼎铭文的时间跨度恰好分属西周的早、中、晚三个阶段,从中我们甚至可以对西周的历史进程形成一些粗浅的认识。上古商周时代留下的文献非常有限,除了《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屈指可数的传世(或早期出土)文献外,就只有同样数量有限,且散落于诸子百家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了。那么,铭刻在商周青铜器上金文文献,就自然要担负起全面勾勒商周社会原貌的重任。而这才是商周青铜器之为国之重器的根本原因。
青铜器上的铭文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有限的传世先秦文献之外,复原西周史事,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正如李学勤在《青铜器与古代史》中所言,“武王时利簋铭文记牧野之战……何尊述兴建成周……厉王时多友鼎记对猃狁战争;……此外,如卫盉、卫鼎、散氏盘等记土地转让,鲁方彝、兮甲盘等记商贾贸易,曶鼎、训匜等记法律诉讼,这些不过是西周重要青铜器中的几个例子,其对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见一斑。”
那么,显而易见,最能体现这些中国商周青铜器所蕴含内在价值的,当属其中丰富铭文所包含的文献信息,以及由其独一无二体量、形制所体现的历史见证感。
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
商周青铜器本身同样散发出的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
谈到商周青铜器的艺术审美,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孔子。他在《论语·八佾》中就表达了对周人文化的赞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所说的“文”,一部分说的是礼仪制度,另一部分则是由这些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正是这些“文化遗迹”不但为我们拼贴上古剪影提供了可能,也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孔子所推崇的周代“文、物”其实也是从之前的“二代”逐步发展而来的。青铜文明在西周所走向的巅峰,离不开前人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积淀。那么要梳理其中的传承关系,我们大体可以从青铜铭文、器形和纹饰这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铭文出现了小盂鼎(周穆王时器,400余字)、曶鼎(周共王时器,434字)、毛公鼎(周宣王时器,497字)这样超过四百字的案例,但这并非一日而成。如孔子所言,西周青铜器铭文字数增长的趋势也可追溯到商代。商代固有甲骨卜祝习俗,但从商末遗存的铜器来看,既有如国博所展出“子龙鼎”一样铭刻族徽的范例,也不乏铭刻数十字“长篇”的范本。
比如,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小臣余犀尊,铭有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卣,盖、器铭共计47字。另有故宫博物院所藏二祀邲其卣铭39字,四祀邲其卣铭42字,六祀邲其卣铭27字。虽然商末铜器铭文通常都只围绕祭祀事件本身,并不作进一步展开,但都可以算作西周长铭文青铜器的先声。而周人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器内铭文华丽、繁富的风格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青铜觥是用于盛酒的礼器。图为凤纹牺觥,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馆藏
其次,器形上讲,周代青铜器继承商代,但其中出现的新的组合变化,则反映了商周人群在观念上的差异。商代青铜器按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三个时期,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殷墟所见铜器,在二里岗时期基本都已现身,其中既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烹煮器鼎、鬲、甗和食器簋、豆,也有觚、爵、尊、卣等酒器、盛水器,以及兵器、工具等等。到了殷墟时期,除了出现了方彝等新型酒器,在其他器物中,圆鼎、方鼎都出现了胎壁变厚的情况,国博所藏子龙鼎、后母戊鼎是其中的代表。
西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器物类型,数量增长的同时,种类有所变化。具体来说,从周初开始烹煮器和食器主要是鼎、簋、鬲、甗,尤其是鼎和簋作为固定礼器组合出现的频率有所提高。这也是这两类器型通常作为铭文载体而为我们所常见的原因。商代流行的豆渐少,但出现了新型的簠,乐器则出现了钟。另外酒器方面,觚、爵、尊、卣等器物类型在周代基本保持不变,但数量已经较商代大幅减少了。其原因大概如《尚书·酒诰》所言,“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周王为了避免重蹈商末贵族酗酒荒政的覆辙,不但发文强调禁酒,还在大盂鼎等器的铭文中屡屡提及,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而且,随着西周中期向后期的发展,当年一度流行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酒器竟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型酒器方面只有壶保留了下来,使后人对商末景象不禁产生无限的怀想。
第三,从纹饰上看,商周之间同样存在继承关系。商代广为流行的饕餮纹、夔纹和鸟纹等主要纹饰基本都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只是细节上而言,鼎、卣等器物上的扉棱较先前更高、也更显著),这造成了两者之间较难区分的情况。幸运的是,大多数时候,周代青铜器内的铭文通常起到了断代的作用。
不过,两者之间同中有异,变化也在悄然间发生。西周青铜器足逐渐改变了商代粗壮的柱足、扁足样式,朝着模仿动物足部的蹄足方向发展。而鼎、鬲、甗等容器的腹部深度和前代相比也变得较浅,器壁也变得愈薄,不如之前厚重。
到西周中期开始,纹饰方面的变化则变得更为显著。首先,纹饰由繁复变得简约,饕餮纹等特征鲜明的动物形象淡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周代制作者对前代生动而具象的鸟、兽动物开始变得陌生,在追求仪式化的过程中,变得神似而非形似。其次,基于同样的道理,用于装饰的细密雷纹等地纹也被省略,到更晚的时代基本不用。此处的变化则与大量铭文的出现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复杂的地纹可能会对铭刻文字造成影响。其三,则是西周窃曲纹、重环纹等简单而重复的纹饰,在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中大量出现。它们或简化自夔龙纹,或取自龟壳鳞甲,用于器物表面装饰填充。按照李学勤的说法,这种变化“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从总体上讲,也基本符合装饰纹样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
ㄐ毌父戊方卣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
商周时代留下如此众多的青铜重器,既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了解,也让后人有机会一睹蕴含于器物之中的上古风韵。从这些古物中,我们得以理解“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得以体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但窥见了商代文明的厚重、象形,也读出了周代文化的文质彬彬。
从商人酒宴上“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的琳琅满目,到周人对“殷鉴”的屡屡反思,从青铜纹饰豪华到质朴的变迁,我们得以绘制出一幅商周交替的动态景象。从周初克商,到中期为南(铜)北(马)交征,再到西周末期的铜料不贡、重器难觅,我们从青铜铭文中勾勒出一段传世典籍之外的商周信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前辈学者对那些国之重器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而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一代的文物研究者通过打破地域、时间和收藏序列的最新的文物研究和展出,也将从更多维度呈现商周青铜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比如,上海博物馆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正推出名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的全新展览。在该展览中,禹鼎和噩侯驭方鼎一同现身,讲述了这个西周古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千古恩怨,也见证了西周王朝从鼎盛走向风雨飘摇的唏嘘之路。
《汉书·郊祀志》提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青铜器作为无可替代的古代遗存,既是上古中国的真实见证,也为我们穿越三千年的历史探索旅程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坐标和导航。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赋予了我们“郁郁乎文哉”的古典气质,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想象之中,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
隹父癸尊,商后期,上海博物馆藏
作者:顾雯(上海博物馆馆员)、张经纬(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编辑:范昕
被誉为“国之重器”商周青铜器凭借的不仅仅是重量
顾雯 张经纬
最近半年以来,商周青铜器备受关注。继上海博物馆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让国博所藏大盂鼎与上博所藏大克鼎联袂亮相,引发广泛关注后,眼下,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这几个大展不约而同聚焦商周时期最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风貌。
商周青铜器素有“国之重器”之称。它们中的不少的确有着惊人的体量,例如子龙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和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重201.5公斤)三鼎,但这毕竟浮于表面。商周青铜器之“重”,更在于极为丰富而厚重的历史积淀,有着从本质上体现其作为国之瑰宝的重要特征。
最能体现商周青铜器内在价值的,当属其中丰富铭文包含的文献信息
其实,单凭一尊毛公鼎就足以破除有关重器之“重”的迷思。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它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为“海内三宝”,但与盂、克二鼎相比,毛公鼎“仅”重34.7公斤,高53.8厘米,口径47厘米,在重量方面就比前两者足足少了一位数字。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毛公鼎却占有一项三鼎之最,那就是字数。据统计,三鼎内壁所刻铭文分别是497(毛公鼎)、291(大盂鼎)和290(大克鼎)字(引自杜迺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毛公鼎铭文字数不但冠绝所有商周青铜鼎,而且也是中国所有已知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按照杜迺松的说法,毛公鼎铭文数量“实可相当《尚书》一篇”。而盂、克二鼎虽不能在青铜器中占据次席(现存字数第二多的,是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散氏盘),但在现存铜鼎中却能紧随毛公鼎之后,分列二三(因为铭刻四百余字的周康王时器小盂鼎,四百十字的周共王时器曶鼎,都已于清末亡佚,仅铭文拓片存世)。
除了铭文字数之外,这些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同样体现了它们不凡的分量。按照原器所铸时间来看,大盂鼎最早,为周康王时器。记载了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康王先是赞美文、武先王,然后总结了商代覆亡的经验教训,告诫盂要引以为鉴,不能沉湎于饮酒取乐。这部分铭文内容恰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吻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次,又授予盂掌管兵戎、民事的权力,辅佐周王管理天下。最后还赐予了他代表权威的鬯酒、命服、车马等等,以及各类奴隶1726人,其中既有夷人的头领十三,也有夷众上千。
而大克鼎年代次之,为周孝王时器。讲述了贵族克继承先祖师华夫的官职,并被周王授予“膳夫”之职,获得诸多田地人口的事情。孝王首先赞扬克的祖先侍奉恭王,因而提拔克为王臣,负责传达王命的要职。接着重申了对膳夫克的任命,详细记录了对他的赏赐,包括礼服、土地和奴隶等等。最后是克叩跪感谢,铸鼎以纪念其先祖师华夫。
三鼎中的毛公鼎相对最晚,为周宣王时器。它记录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改变西周后期的种种弊政和不利局面,策命重臣毛公,监督各种政令的发布和实施。希望在毛公的忠心辅佐下,使国家免于衰颓的境地。最后为了体现对毛公的尊重,宣王还赐给他极为丰厚的赏赐,包括各种宝物和贵重的车马器。而毛公为了回谢周王,特意铸鼎记录此事。
三鼎铭文的时间跨度恰好分属西周的早、中、晚三个阶段,从中我们甚至可以对西周的历史进程形成一些粗浅的认识。上古商周时代留下的文献非常有限,除了《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屈指可数的传世(或早期出土)文献外,就只有同样数量有限,且散落于诸子百家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了。那么,铭刻在商周青铜器上金文文献,就自然要担负起全面勾勒商周社会原貌的重任。而这才是商周青铜器之为国之重器的根本原因。
青铜器上的铭文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有限的传世先秦文献之外,复原西周史事,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正如李学勤在《青铜器与古代史》中所言,“武王时利簋铭文记牧野之战……何尊述兴建成周……厉王时多友鼎记对猃狁战争;……此外,如卫盉、卫鼎、散氏盘等记土地转让,鲁方彝、兮甲盘等记商贾贸易,曶鼎、训匜等记法律诉讼,这些不过是西周重要青铜器中的几个例子,其对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见一斑。”
那么,显而易见,最能体现这些中国商周青铜器所蕴含内在价值的,当属其中丰富铭文所包含的文献信息,以及由其独一无二体量、形制所体现的历史见证感。
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
商周青铜器本身同样散发出的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
谈到商周青铜器的艺术审美,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孔子。他在《论语·八佾》中就表达了对周人文化的赞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所说的“文”,一部分说的是礼仪制度,另一部分则是由这些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正是这些“文化遗迹”不但为我们拼贴上古剪影提供了可能,也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孔子所推崇的周代“文、物”其实也是从之前的“二代”逐步发展而来的。青铜文明在西周所走向的巅峰,离不开前人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积淀。那么要梳理其中的传承关系,我们大体可以从青铜铭文、器形和纹饰这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铭文出现了小盂鼎(周穆王时器,400余字)、曶鼎(周共王时器,434字)、毛公鼎(周宣王时器,497字)这样超过四百字的案例,但这并非一日而成。如孔子所言,西周青铜器铭文字数增长的趋势也可追溯到商代。商代固有甲骨卜祝习俗,但从商末遗存的铜器来看,既有如国博所展出“子龙鼎”一样铭刻族徽的范例,也不乏铭刻数十字“长篇”的范本。
比如,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小臣余犀尊,铭有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卣,盖、器铭共计47字。另有故宫博物院所藏二祀邲其卣铭39字,四祀邲其卣铭42字,六祀邲其卣铭27字。虽然商末铜器铭文通常都只围绕祭祀事件本身,并不作进一步展开,但都可以算作西周长铭文青铜器的先声。而周人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器内铭文华丽、繁富的风格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其次,器形上讲,周代青铜器继承商代,但其中出现的新的组合变化,则反映了商周人群在观念上的差异。商代青铜器按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三个时期,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殷墟所见铜器,在二里岗时期基本都已现身,其中既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烹煮器鼎、鬲、甗和食器簋、豆,也有觚、爵、尊、卣等酒器、盛水器,以及兵器、工具等等。到了殷墟时期,除了出现了方彝等新型酒器,在其他器物中,圆鼎、方鼎都出现了胎壁变厚的情况,国博所藏子龙鼎、后母戊鼎是其中的代表。
西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器物类型,数量增长的同时,种类有所变化。具体来说,从周初开始烹煮器和食器主要是鼎、簋、鬲、甗,尤其是鼎和簋作为固定礼器组合出现的频率有所提高。这也是这两类器型通常作为铭文载体而为我们所常见的原因。商代流行的豆渐少,但出现了新型的簠,乐器则出现了钟。另外酒器方面,觚、爵、尊、卣等器物类型在周代基本保持不变,但数量已经较商代大幅减少了。其原因大概如《尚书·酒诰》所言,“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周王为了避免重蹈商末贵族酗酒荒政的覆辙,不但发文强调禁酒,还在大盂鼎等器的铭文中屡屡提及,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而且,随着西周中期向后期的发展,当年一度流行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酒器竟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型酒器方面只有壶保留了下来,使后人对商末景象不禁产生无限的怀想。
第三,从纹饰上看,商周之间同样存在继承关系。商代广为流行的饕餮纹、夔纹和鸟纹等主要纹饰基本都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只是细节上而言,鼎、卣等器物上的扉棱较先前更高、也更显著),这造成了两者之间较难区分的情况。幸运的是,大多数时候,周代青铜器内的铭文通常起到了断代的作用。
不过,两者之间同中有异,变化也在悄然间发生。西周青铜器足逐渐改变了商代粗壮的柱足、扁足样式,朝着模仿动物足部的蹄足方向发展。而鼎、鬲、甗等容器的腹部深度和前代相比也变得较浅,器壁也变得愈薄,不如之前厚重。
到西周中期开始,纹饰方面的变化则变得更为显著。首先,纹饰由繁复变得简约,饕餮纹等特征鲜明的动物形象淡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周代制作者对前代生动而具象的鸟、兽动物开始变得陌生,在追求仪式化的过程中,变得神似而非形似。其次,基于同样的道理,用于装饰的细密雷纹等地纹也被省略,到更晚的时代基本不用。此处的变化则与大量铭文的出现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复杂的地纹可能会对铭刻文字造成影响。其三,则是西周窃曲纹、重环纹等简单而重复的纹饰,在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中大量出现。它们或简化自夔龙纹,或取自龟壳鳞甲,用于器物表面装饰填充。按照李学勤的说法,这种变化“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从总体上讲,也基本符合装饰纹样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
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
商周时代留下如此众多的青铜重器,既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了解,也让后人有机会一睹蕴含于器物之中的上古风韵。从这些古物中,我们得以理解“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得以体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但窥见了商代文明的厚重、象形,也读出了周代文化的文质彬彬。
从商人酒宴上“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的琳琅满目,到周人对“殷鉴”的屡屡反思,从青铜纹饰豪华到质朴的变迁,我们得以绘制出一幅商周交替的动态景象。从周初克商,到中期为南(铜)北(马)交征,再到西周末期的铜料不贡、重器难觅,我们从青铜铭文中勾勒出一段传世典籍之外的商周信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前辈学者对那些国之重器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而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一代的文物研究者通过打破地域、时间和收藏序列的最新的文物研究和展出,也将从更多维度呈现商周青铜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比如,上海博物馆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正推出名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的全新展览。在该展览中,禹鼎和噩侯驭方鼎一同现身,讲述了这个西周古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千古恩怨,也见证了西周王朝从鼎盛走向风雨飘摇的唏嘘之路。
《汉书·郊祀志》提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青铜器作为无可替代的古代遗存,既是上古中国的真实见证,也为我们穿越三千年的历史探索旅程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坐标和导航。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赋予了我们“郁郁乎文哉”的古典气质,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想象之中,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
(作者分别为上海博物馆馆员;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 文汇报
青史斑斑|鼎盛千秋:西周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
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湾的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目前,上海博物馆将其馆藏的大克鼎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大盂鼎合璧展出,这是两鼎时隔十四年之后再度聚首上海。大克鼎、大盂鼎不仅独具历史与艺术价值,其背后的故事更彰显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守护之心。
鼎今天还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相当于夏、商、周三代,这一时代产生了工艺高超、种类繁多的青铜器,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诚如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言,“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而祭祀与战争正是当时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
今天当我们参观各地博物馆时,不仅能见到许多青铜器,而且常常为青铜器的名称与功能而难住,它叫什么,它有什么用,今人距离青铜时代已有几千年,提出这些问题实属正常。青铜时代留给今人的遗产,最大的一笔来自青铜鼎。鼎也许是今人最熟悉的青铜器,不仅因为它较之其他青铜器更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也因为有关鼎的成语、典故仍为我们使用。
鼎是一种饪食器,后来发展为礼器,一般分为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大克鼎、大盂鼎都是三足圆鼎,而目前我国已知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则是四足方鼎,足有832.84千克重。青铜鼎上常有精美的纹饰,一些青铜鼎上还有铭文,记载制作此器的由来,表达希望子子孙孙永存此器的愿望。
我们常用“一言九鼎”形容一个人说话有分量,倘若知道“九鼎”的内涵,便知这“一言”的分量有多重了。在西周的礼法制度下,不同社会阶层在着装、出行、器物的使用上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具体到鼎的使用上,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九鼎是最高的规格,没有比九鼎更高的礼遇了。
九鼎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可以追溯到夏禹。那时天下划为九州,传说夏禹用九州贡献的青铜铸成九鼎,将各地奇怪之物刻在鼎上,其用意是“使民知神奸”。百姓进入川泽山林采集生活物资时,因为已从九鼎上知道那些可能危害自己生命的奇怪之物的模样,就能很好地予以规避。细究禹铸九鼎的含义,一方面九鼎代表了夏朝对九州的控制,另一方面九鼎是国家与百姓沟通的方式,国家出于对百姓的爱护,善意提醒哪里存在危险。
九鼎在夏商周三代间的传承,使其具有了证明权力正当性的功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想必读者不陌生,但我们只记住了楚庄王的威风凛凛,却忘了王孙满的一番话揭示了九鼎深刻的内涵。楚庄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答道:“在德不在鼎”。以前夏桀昏庸,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这便是“革故鼎新”,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创造新事物。王孙满认为“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九鼎属于有德者,有德者能顺应天命,能以民为重,使上下协和,使邦国巩固。
铸造于西周治世,见证青铜时代的辉煌
大克鼎、大盂鼎都是西周时代的青铜重器,这里的“重”当然不仅指重量,也指其在礼仪上的重要地位、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两鼎原本都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盂鼎应征北上,此后安家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两鼎京申相望,镇护南北,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相聚,今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两鼎再度相聚,目前在上海展出,之后还将在北京展出。
两鼎中铸造时间更早的是大盂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康王在位时。周康王与父亲周成王共同开创了“成康之治”,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大盂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大盂鼎是圆鼎,口沿下装饰有一圈饕餮纹带,粗壮的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器的经典式样。使这件青铜器具有非凡价值的是鼎腹内壁铸刻的291字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周康王向盂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立国的经验以及商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提到商朝大小官员无不沉湎于饮酒,致使政事败坏,人民失望,告诫盂应敬畏天命,效法祖先南公,忠心辅佐王室,认真处理政事。第二部分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盂的具体内容,盂感谢周康王的赏赐,并铸鼎以祭祀祖先南公。这篇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且字迹端庄典雅,历来为书法家推崇。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周孝王在位时,他在位时最大的功绩是对西戎作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戎对周的攻势。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其纹饰较大盂鼎更加丰富且更具动感,口沿下仍装饰一圈变形兽面纹,每组变形兽面纹之间装饰扉棱,腹部装饰一圈宽大的波曲纹,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兽面纹,兽面鼻梁装饰扉棱。
大克鼎腹内壁铸刻一篇290字的铭文,由这篇铭文可知作此器者是一个叫克的贵族,他的身份是周孝王的一位“膳夫”,即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但克的职责不止于此。大克鼎铭文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克对祖先师华父的称颂,师华父辅佐王室有功,施惠政于民,周王感念其功劳,命克负责上传下达王的命令。第二部分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克感谢周王的赏赐,铸鼎以祭祀祖先师华父,希望此器“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是青铜铭文经典的结句,包含着对永远延续家族荣耀的期待。但永恒从来难以实现,家族的升沉起伏才是常态,盂和克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大盂鼎、大克鼎历尽劫波后存续了下来。
将鼎埋在地下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
我们今天能在博物馆中一睹大盂鼎、大克鼎的风姿,要感谢潘达于女士的守护与捐赠。两鼎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出土于陕西,有太多同时代出土的中国文物,或毁于战火,化为灰烬,或被偷走劫走,永远离开了故土。大盂鼎、大克鼎能够完好留存在国内,实非易事。
一般认为,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任村。岐山、扶风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出土了许多青铜器,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大克鼎出土后,便为当时著名金石收藏家、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大盂鼎的流传过程比较复杂,它最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之后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去,他又将大盂鼎出售给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恰好宋金鉴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发现自己的心爱之物出现在市场上,他花了三千两白银赎回。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宋家家道中落,大盂鼎转手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保恒,不久他就把大盂鼎转送给了左宗棠。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遭官场流言中伤,幸得潘祖荫搭救,左宗棠为感谢潘祖荫,将大盂鼎赠送给了他。
至此,大盂鼎和大克鼎都归潘祖荫拥有,潘祖荫对此颇为得意,表示“天下三宝得其二”。潘祖荫死后,其弟将两鼎运回老家苏州收藏,并且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奈何两鼎名气太大,仍不断遭人觊觎。担任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端方以收藏金石为乐,他想了许多办法要从潘家获得两鼎,均以失败告终。如果两鼎归端方所有,我们难以预料两鼎是否还将留在中国。1911年,端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新军杀死,他的后人因为生计无着,将端方的一批青铜器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后,面对美国人高价收购的利诱,国民党要员借鼎展出的要求,潘家均予以拒绝。
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日本人早已知道潘家收藏着大盂鼎和大克鼎,日军屡次破门而入搜查,均未找到。这时操持潘家的是一位叫潘达于的女子,她原姓丁,嫁给潘祖荫之孙后改夫家姓,丈夫不久病故,护持潘家文物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个弱女子的身上。在苏州沦陷前,潘达于已预感到文物不再安全了,于是在家中挖了一个大坑,将大盂鼎、大克鼎和其他一些文物埋入其中。两鼎就这样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
1951年,得知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办中,已定居上海的潘达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大盂鼎、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所有人都能在博物馆中看到这两件珍宝。文化部接受了潘达于的捐赠,面对国家两千万元(旧币)的奖励,潘达于全数捐赠,用以支持抗美援朝。潘达于此后在1956年、1963年、197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珍贵文物资料近五百件。
大盂鼎、大克鼎,既见证了青铜时代的辉煌,又照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伟大的文明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不断的守护而能赓续,伟大的文明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淬炼中而升华更新。(罗慕赫)
国之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重聚,上博将展出21件有铭青铜鼎
视频加载中...
2021年6月16日上午,“回娘家”的大盂鼎与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重聚。
盂克双鼎重聚。左为“大克鼎”,右为“大盂鼎”。
经过40分钟的开箱、点交、移动,微调位置后,这件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的大盂鼎终于回到娘家,与上博“镇馆之宝”大克鼎重聚。
昨晚“大克鼎”布展时,“大盂鼎”就在一旁的箱子里静静等候。
开箱。
国博工作人员进行点交。
出箱的“大盂鼎”慢慢移向展台。
微调位置。
撤去足垫。
两件青铜鼎相隔一米,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助理馆员刘锴云分别介绍,大盂鼎腿细长一些,是西周早期鼎的特点之一;大克鼎是西周中期的鼎,腿粗短一些,而且有点“外八”字,到了更晚的东周时期,鼎足外撇得更厉害,甚至会像兽蹄一样。
大盂鼎内壁铭文。
大克鼎内壁铭文。
大克鼎、大盂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是迄今为止有铭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于十九世纪先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为潘家珍藏,历经战乱,世代守护。
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女士代表家族将此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盂克双鼎,镇守南北,见证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回顾一下昨晚大克鼎“上楼”的程序。
拆去玻璃罩。
移至摆渡车。
坐电梯上楼。
上展台。
微调位置。
上海博物馆将于6月18日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开幕式,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展览中的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
上博、国博工作人员记录下这历史性的时刻。
栏目主编:张春海 文字编辑:张驰 图片编辑:张驰 编辑邮箱:8903168@qq.com
上观新闻 蒋迪雯 摄影报道视频拍摄 蒋迪雯 视频剪辑 杨文瑛
来源:作者:蒋迪雯
以上就是小编对于问题和相关问题的解答了,希望对你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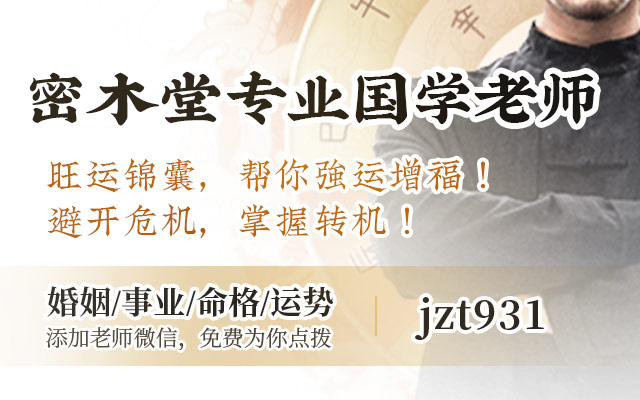
免责声明
以上文章转载自互联网,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建议,也不代表密木堂赞同其观点。 如有侵权请联系Bear1023@189.cn,提供原文链接地址以及资料原创证明,本站将会立即删除